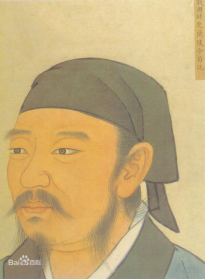
荀况,即荀子,字卿,又称孙卿,赵国(今山西省南部)人。约生于公元前318年,卒于前238年。他曾两次任兰陵令,晚年定居兰陵潜心著书立说,逝世后葬在今苍山县兰陵镇东南。
当时,中国奴隶制己经瓦解,封建制正在确立,各诸侯国政治、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,结束战国以来“诸侯异政,百家异说”的局面,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,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荀况顺应历史潮流,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,为实现中国统一而广作舆论准备,成为战国末期杰出的政治理论家、教育家和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。
荀况年少时英俊而富有才华,15岁便到齐国游学。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官是当时各国学者云集、开展百家争鸣的著名场所。荀况在此游学期间,有机会听取各学派名师的讲演,从而多方面地了解和掌握了他们的学术观点,在各派学术思想的熏陶中成长为一名博学者。
他曾企图说服执政的齐湣王实行王道政治,争取统一天下;同时又警告说,如不小心治国,就有被人吞并的危险。但齐湣王居功自傲,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。相反,在灭掉宋国以后,又南侵楚国,西侵三晋,还想吞并周朝称天子,谁劝谏就杀死谁,致使群臣纷纷离去,荀况也只得遗憾地到楚国去考察访问。不久,齐湣王果然被燕国打败,身死国危。 齐襄王即位后,年已60多岁的荀况,从楚国又第二次到齐国讲学。由于他在学术和品德上都深孚众望,被齐襄王封为“列大夫”,并三次被稷下学者推为“祭酒”(学宫领袖),尊奉他“最为老师”。这时他的门人弟子很多,著名法家韩非、李斯都是他的学生。
后来,他看到秦国日益强盛,是统一中国的希望所在,便西游入秦,对秦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自然形势和风俗民情进行了实地考察,并入秦都咸阳拜见了秦昭王和秦相范睢,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扬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,社会秩序良好,矛盾比较缓和,对外来的人恭敬有礼,中央集权的政治比较稳定,官吏执法严肃认真,不敢结党营私,政府办事效率较高,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,已接近“治之至”的程度了。他还向秦昭王陈述统一天下的大计,但没有得到采纳。
当他离开秦国在回答学生李斯的问题时,又尖锐地指出:秦国4代强盛,但它又经常担心天下的人会联合起来攻打自己,这是“末世之兵”。秦国不用仁义治国,只能成为霸者,这也正是它的短处。历史证实了荀况的观点是正确的,倘若秦国不完全依靠暴力,也采用礼治,那么统一天下之后也许不至于很快灭亡。经过这次考察,荀况的社会经验更加丰富了,眼界更加开阔了,对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他的法家思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离秦后荀况又回到齐国,这时齐国朝政由“君王后”控制着。他曾向齐相陈述齐国面临的严重局面,并对“女主乱之宫”、“诈臣乱之朝”、“贪吏乱之官”等现象进行揭露,因此遭到谗言毁谤,便于前255年到了楚国,被楚国丞相春申君任为兰陵令。因受人诽谤,又返回赵国,赵孝成王授他为上卿。在赵居留期间,他与临武君曾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,他的军事才干不仅使赵王,就连这位久经战阵、名扬诸侯的名将临武君也被折服了。后来春申君再度敦请荀况回楚,让他继任兰陵令。
前228年春申君被人害死,荀况也遭废黜,便定居兰陵,潜心著书立说。享年90多岁,死后葬兰陵。其著述宏富,据记载,在汉初流传的有322篇,后来被汉儒刘向删去290篇,仅存32篇,经后人编辑成《荀子》书。

荀子墓
荀况在对先秦“诸子百家”的思想学说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,提出了一套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新理论,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,达到了先秦时期的最高水平。
荀况政治主张的核心是“天下为一”。“臣使诸侯一天下”,“四海之内为一家”。他在游历各国时,总是反复宣传这个主张,劝导当时比较强盛的诸侯国国君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。为此,他提出了3条具体主张:
一是隆重礼法,就是既要讲礼治、德治,又要讲法治。他把刑法与礼义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,同作为治国的根本。他认为“明礼义以化之”,“重刑罚以禁之”,天下就可转而为善,政治上就可趋于治。他把礼治与政治结合起来。这是兼采了儒、法两家之长,纠正了儒、法两家之短。
二是尚贤使能。主张“论德而定次,量能而授官”,荐贤才要“外不避仇,内不阿亲”,举能者要“不恤亲疏,不怕贵贱”,提出了任人唯贤、唯能的选择官吏的办法。
三是平政爱民,主张君主要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。他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和水的关系,说:“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。”甚至说:“天之生民,非为君也;天之立君,以为民也。”他看到了能否处理好与民的关系,对建立和维持封建秩序是至关重要的。这3个方面互相结合,就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治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,构成了实现“天下为一”的大政方针。
荀况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上,对殷周以来的“天命观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他把“天”解释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界,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,既不是神,也不是上帝,列星的旋转,日月的递明,四时的代谢,阴阳的变化,风雨的施降等等都是自然现象,因此他反对迷信、巫祝、祈祷,认为诸如星坠、木鸣、日月食等怪异现象没有什么神秘,更不必害怕。
他还认为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,天不以帝王的更替和政治的好坏为转移,也不因为人不喜欢寒冷就去掉冬天,因为人怕走路就缩小土地的辽阔,而是有着自己变化的客观规律。针对当时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的唯心主义观点,他明确地提出了必须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命题。就是说,天和人要加以区别,天有天的功能,人有人的作用,两者互不相干。
不仅如此,他还进一步提出了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光辉思想。他认为人在自然界面前,决不能消极无为,坐等天的恩赐,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,利用和控制自然界为人类造福。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,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,闪烁着唯物论的战斗光辉,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,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。
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,荀况建立起自己唯物主义的认识论。他认为,人生来就具有认识能力,而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,人有能知之才,物有可知之理。他的高明处还在于他把人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是“天官簿类”阶段,即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、认识各种事物的属性,形成感觉。第二个阶段是“心有征知”阶段,即通过思维器官“心”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、辨别、验证,形成概念和判断,使感性认识进入到理论认识。只有把这两个阶段结合起来,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道理,这就是“以心知道(规律)”。
荀况分析了先秦各家的理论,指出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,能够“解蔽”,必须发挥“心”的理性思维作用。心只有“虚壹而静”,即虚心、专心、静心地思维,去掉偏见、成见,才能校正错觉、幻觉,验证知识,达到“知道(规律)”的目的。
荀况还特别强调获取知识必须通过主观努力,通过艰苦的学习、积累。为此他写了《劝学》篇,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“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,“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”这些鼓励人们好学上进、奋发图强的千古名句,就出自荀况。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强调在实际中学习,要学用一致,“知之不若行之,学至于行之而止矣”,学得的知识必须经过实际的验证。在知行关系问题上,他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。
在逻辑学上,荀况批评了春秋战国以来名实关系问题上的种种错误,辩证地论证了名实关系。他说:“制名以指实”,“实”是客观存在,是第一性的,“名”是客观事物的反映,是第二性的,名是由实派生的。主张名实相符,听到名称就知道是什么事物,确定名称就能区别是什么事物。荀况还探讨了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,对先秦逻辑作出了总结性的概括,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形式逻辑学。
在人性论的论争中,荀况提出了“性恶论”。他认为,人的本性是恶的,人能够为善,是后天人为改造的结果。认为人性本恶,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;但他又认为,正因为恶,才需要礼义、法、刑罚,才需要学习和教育。通过人为的教育,完全可以改变“性”,即使普通的老百姓,也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、贤人。他的“性恶论”,否认了孟轲“性善论”的天赋道德论,强调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,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,因而仍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在社会历史观方面,荀况提出了“明分使群”的观点。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合群,组成社会,联合成一个整体。人组织起来以后,虽然力不如牛,跑不如马,但仍可以服牛乘马,征服自然。而要组成一个社会,就要“明分”,“明分”的标准则是“礼义”,“制礼义以分之”,确定上下职分和等级差别,把人们的社会地位固定下来,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”,“农农、士士、工工、商商”,不管朝廷的君臣关系,还是家庭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的职业关系都各守其分,从而建立起封建统治秩序。他的这种观点不仅区别了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差异,而且肯定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,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
特别是他看到,人只有通过社会组织,利用集体力量,才能支配自然,这是他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中的运用和深化,因而是十分深刻的。荀况还针对孟轲“法先王”的口号,针锋相对地提出“法后王”,就是要效法当今,学习当世的君主,主张革新,反对倒退。他高度赞扬推行法治的秦国:“威,强乎汤武;广,大乎舜禹。”远远超过历代“先王”。他这种厚今薄古和进步历史观,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要求。
荀况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。他长期讲学,学生极多,培养出了像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、秦国丞相李斯这样的理论家和政治家。据说荀况死后,其弟子“著书布天下”。他还是传经大师,汉代传授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的学者,不管是今文家、古文家,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出师于荀况。他所总结的一些学习方法、经验和规律,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。
总之,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思想家,对先秦各家各派的哲学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总结,他解诸子之蔽,取百家之长,在综合百家的基础上,建立起自己集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。这个体系广博宏深,包含丰富的内容,涉及到自然观、社会观、人性论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以及认识论、逻辑学等各个领域。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,他的思想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从韩非到王充,再到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王夫之,直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,都从他的思想体系中吸取过积极的营养。清末思想家谭酮同曾说过:“二千年之学,皆荀学也。”足见其影响之大。当然,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,他的哲学体系中仍存在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杂质,这是需要批判的。
 通知公告:
通知公告:
 通知公告:
通知公告: